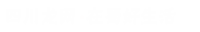如果被抓进精神病医院了,怎么才能证明自己不是神经病?以下的故事告诉你,一个在精神病院关了17年的人,是怎么样自救成功的 。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 。凌晨四点,徐为准时起床,把最好的衣服和鞋子一一穿上,脑子里一遍遍彩排接下来会发生的所有可能性和要注意的细节 。另一间房间里,他的女友春春也已准备妥当 。半个小时后,徐为和春春手牵手走到康复院门口 。他们将要敲开值班室的门,告诉值班阿姨,他们要去买早点 。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每天都严格遵守这个流程:凌晨四点起床,四点半一起走到康复院门口,等值班阿姨开门放他们出去买早点 。按照惯例,值班阿姨会打开铁门,让他们出去 。因为她知道,他们不久后就会回来,并且多带一份早点给自己 。早春的上海,凌晨仍是簌簌的冷 。徐为和春春紧紧挨着站在铁门前,徐为个子很高,像小学生一样双脚并拢站地笔直,但仍然挡不住已经微微驼起的背 。他紧紧攥着女友的手,放在自己身后 。此刻,他们正盯着铁门上的锁,心里无比紧张 。就在这扇铁门边上的墙上,有一块方形的金属牌子,上面写着:“精神康复院 。”为这一刻,他们已经准备了十年 。今天,值班阿姨会照例给他们开门吗?二2000年10月,徐为乘坐的飞机落地广州白云机场 。大约是更早的10年前,他拿着中专文凭钻进出国潮 。刚落地澳洲,发现报读的语言学校是山寨的,交了钱的住处也联系不上,还没有开始新生活,就背上了黑身份 。10年间,徐为一边打黑工,一边争取合法居留,但最终还是被遣送,蹭上了一张免费的回国机票 。徐为并不想回上海老家 。在国外什么名堂都没有混出来,碰到熟人肯定觉得丢脸 。倒不如就留在广州,把日子过好一点再回去 。但是那种感觉又来了 。他脑子里抑制不住地出现了一行字幕:“这里不该有这么多人呀,这里面好像有人在跟着我 。”周围的人好像都在偷看他、试图包围他,走近又像没什么事一样散开了 。徐为很希望能够抓住一个人问:“你们到底是为什么跟着我?”再细看,周围都只是行色匆匆的路人 。这种感觉对于徐为已不再陌生了,仍让他感到惊慌无措 。于是他决定回上海 。就这样,十年之中不曾与家里有很多联系的徐为,空降回家 。回到家,徐为开始为自己在澳洲的经历申诉,前前后后跑了澳大利亚领事馆、华侨办公室、外事办等好几个部门,但到都没有音信 。他经常打电话给在澳洲的朋友,电话费都花了两千多块钱 。徐为的大哥看到他这种焦躁的状态,觉得他一定是在国外把脑子呆坏掉了,发精神病了 。2001年春节过后不久,徐为刚回家不到一年,就被大哥和父亲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 。这是徐为第一次入院,在那里,他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三这种被跟踪的感觉早在1994年,徐为还在澳洲的时候就出现了 。布里斯班的木星赌场,在连续三个半月里,徐为像有了金手指一样,逢赌必赢,每次至少赢5000澳币,几个月里徐为赢了20多万澳币 。那时他想赢到30万就回国,家里兄弟三人每人都能分到10万澳币 。但就像过山车,爬到顶峰后接着便是急转直下,而徐为在赌场里坐的这趟过山车,顶峰就是20多万 。那天徐为又一次干脆利落地赢了近2万块 。他想乘胜追击,但突然感觉到牌桌上有人出千作假,随着作假的小动作,牌势也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是冲着他来的 。有一股不可抗的力量在他眼前,要把刚才的好牌和好运一笔一笔地抹去 。他乱了阵脚,把大把大把筹码推上牌桌,一直输,输光了手里的钱,还去银行取了钱,回到牌桌上继续输 。就这样,两三天的时间里,几个月赢来的钱转眼成空 。赌桌上的输赢只是一时,但那种感觉却溢出赌场,渗入到生活的其它方面 。他去找工作,觉得是有人在背后帮助他,安排他找到了这份工作;他走在路上,就感觉有人跟踪他;他打电话,感觉电话被监听了……如果说最初在赌桌上的那种感觉只是一个小雪球,那么这个小雪球很快就如失控一般越滚越大 。徐为开始觉得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人操控,每一件事情之间都有联系 。即便是那些早已模糊的往事和故人,再想起来似乎也都有不寻常的隐喻 。这种感觉渐渐把他的记忆、猜测和确有的经历都杂糅到了一起 。别人都说徐为病了,精神病,但他自己不这样认为 。真正有精神病的人会确信自己感觉到的就是真实发生的,但他并没有这么确信 。徐为的这些感觉都只是猜测——可能是有人在监视我,可能是有人帮我安排了工作……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猜测 。他渐渐被巨大的谜团所围困,即便在“有没有病”这件事上,他都不是百分百确定 。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没有病,有时候又会问这到底是不是因为他有病 。但在别人看来,这就是精神病,最多也只是病得轻和病得重的区别 。四2001年春,徐为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 。那是一家二级医院,入院后有诊断,有医生开药,每隔几天医生都会和病人谈谈,家属随时可以来访,看起来非常正规 。但就是这样一家医院,在徐为入院的第一天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小护士要给徐为打针,他不肯,于是来了另一个人把徐为打了一顿,痛得他睡都睡不着 。挨了这顿打,徐为就获得了住院的第一条攻略:如果不想挨打,自己就得太平一点,不能跟人家搞事情 。徐为逐步意识到精神病院其实是一个等级严格的独立王国 。医生和护士是顶层阶级 。医生掌握着开药的大权,谁不听话就给谁多吃点药 。与病人接触最频繁的是护士,从二十几岁到四五十岁的都有,像帝王一样 。有一次,一位病友说话稍微大声了一点,年轻的小护士立刻转过头,脸一板,说:“你知道规矩的啊 。”声音不大,但那个病友马上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了 。领教了几次医生护士的威严,徐为就获得了在这里住院的第二条攻略:医生护士说什么都必须听,不听不行 。位于独立王国第二阶层的是病头——就像监狱大牢里有牢头,精神病院里有病头,病头就是那些享有特权的病人 。那些听护士的话,让护士比较看重的人才能成为病头 。徐为入院第一天不肯打针的时候,就是医生叫病头把徐为打了一顿 。医生和护士让病头做一点上不了台面的事,而病头多少能从医生护士那里得一点好处 。至于底层的病人能不能团结一致反抗呢?基本是不可能的 。徐为刚入院不久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病友和病头吵架,病头动手打了这个病友 。医生护士没有惩罚打人的病头,而是把被打的年轻病友送上电麻椅 。当时,住院经验还不丰富的徐为仍有勇气说两句公道话 。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打抱不平地和医生说:“明明他是被打的,你们放着打人的人不管,让被打的坐电麻椅,你们讲不讲道理?”但只有徐为胆子大,其他病友都不敢作声 。后来住院的经验值高了,徐为也就认清了在这个独立王国里并没有道理二字 。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徐为也不作声了 。病友怪他:“你为什么不来帮我?”他说:“我来帮你也起不到作用呀,只是多一个人被打而已 。”这是徐为记下的第三条住院攻略:作为一个底层病人,只能昧着良心、事不关己 。那能不能向前来探访的家属求助呢?经徐为观察,十个人里面九个人的家属是不会给予帮助的——家属就是想把人关在医院里,他们不会管人会不会在医院里被打 。太太平平地住了一年,治疗得差不多了,医生对他说:“你可以走了 。”没有人来接徐为,医院也没有要求一定要有人来接才能让他出院 。那时是2002年,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一年的徐为问别人借了一块钱,独自出院,坐公车回家了 。如果那时他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一定会感叹这一次住院的时间之短,更会惊讶这一次出院是如此简单 。五出院后,徐为和父亲住在一起,找了一份在工厂车间的工作,每个月1500块钱 。后来在涨工资的事情上和老板没谈拢,这份工作也就不做了 。徐为阔别家乡十年,父子感情本来就比较淡漠 。父亲在心里怪责他不珍惜工作的机会 。徐为则不满父亲把日子过得糟心,连续三个月都吃青菜豆腐冬瓜汤不带一点变化 。在2003年7月的一天,父子之间发生了争吵,直接导致徐为第二次被送进精神病院 。那场争吵之后,父亲去找了居委会 。不知是因为争吵真的过于激烈,还是因为居委会一听说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住过精神病院的人”,就觉得如临大敌,居委会又找了派出所 。最后,父亲、哥哥、居委会和派出所一起把徐为送去了精神病院 。看到这么大的阵仗,徐为自知没有能力反抗,便识相地跟着走了 。这一次,他被送去了一个离家很远的精神康复院 。入院的那天,只办了简单的手续,父亲和哥哥就走了 。医生把他送进康复院的第一间小屋子,收走了他身上的三五百块钱,把门一关,就不管他了 。这间房间里就一张床,外面有铁门,徐为在里面住了一个多星期 。一有机会他就问医生:“我到底有什么病?”医生不搭理他 。不过药倒是很快跟上了,徐为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吃的是氯丙嗪,这一次就继续吃氯丙嗪 。在徐为一而再、再而三的追问下,医生勉强对徐为进行了一次会诊 。但就随便问了点问题,也没出什么结果 。会诊之后,徐为被分到了普通病房,和几个病友合住 。这家精神康复院和徐为第一次住的那家精神病院挺不一样 。康复院里的诊断和治疗都没有那么正规,但整体上也没有那种等级森严的气氛 。康复院对病人的管理比较松散,病友们平时能抽抽烟,病友之间还能做一点倒卖香烟的小生意 。如果说之前那家医院是为了治病,这家则更像是精神病人的长期收容所 。一开始,居委会的人会陪父亲来康复院探访 。每次他们来,徐为都会强烈要求出院回家 。居委会的阿姨嘴上答应帮他看看,但看着看着连人也不出现了 。父亲年纪大,不认识去康复院的路,没有居委会的人陪着,便也不来了 。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中午11点午饭后午休,下午1点半起床,3点45分吃晚饭,4点回房睡觉,算下来一天要睡超过14个小时 。徐为就在这样的作息里开始了看不到尽头的康复院生活 。住在这里面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每天睡超过14个小时,再正常的人都能睡出精神病来;如果不睡觉,在白墙四壁的房间里就只能发呆瞎想,想多了精神病就更严重了 。有时他觉得康复院的作息并不是为了帮助里面的人康复,而是在卖力地为康复院存在的意义服务 。看不到出路的徐为想到了逃 。剧照 | 《飞越疯人院》但徐为觉得那些被抓回来的病友都是脑子一热就翻墙出去了,身上没钱,脑子里没计划,在街上游荡两天,没有吃没有住,想想还是回来吧 。还有一些病友是逃回家的,没两天又被家人送回来了 。看多了这种出逃未遂,徐为便明白,即使翻过了康复院的墙头逃出去,外面还有看不见的墙头等着他 。如果想逃出去,在外面生根,永远不回来,就要沉住气,长远规划,缜密安排 。六长远规划的第一步,就是要在康复院里活成一个模范病人的样子 。对住精神病院已颇有门道的徐为知道,只有活成一个人畜无害的模范病人,后面的一切才有可能 。在康复院里有一位自建立之初就住进来的资深病友,平时兼任康复院的总务——负责给病人发发东西,分分点心 。总务是个外开放的病友,周末可以回家,周末结束再自行回来 。随着康复院里病人数量增多,总务需要一个帮手,这就选中了模范病人徐为 。徐为开始帮总务做事,渐渐就像康复院里的半个工作人员,也和医生护士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医患之间的人际关系 。有了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人际关系,徐为的长远规划第一阶段进行得顺利 。长远规划的第二步,是要拿回自己的证件 。徐为的身份证在入院的那天就被收走了 。他知道,要想在逃出去之后顺利地生活,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证件拿回来 。因为早早就怀有这样的想法,当康复院组织病人重拍身份证照片的时候,徐为立刻抓住机会,拿回了自己的身份证 。除了运气之外,也多亏了好病友人设让康复院的医护们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对他的戒心 。长远规划的第三步,钱 。钱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过去那些逃出去又被送回来的病友,多半是因为身上没有钱,所以无法在外面独自生活 。但是,在康复院里要怎么挣钱呢?病友们之间最抢手的东西是香烟 。康复院里物资匮乏,连个小卖部都没有,想要抽烟,就只能想办法从康复院外买进来 。徐为看准了这个商机,靠着给总务做帮手时建立起来的人脉,拜托护士们和总务帮他买烟带进康复院,他再把这些烟转手卖给病友,从中赚个差价 。在康复院里,香烟几乎就是硬通货 。所以买烟这个特权不仅让徐为赚到了钱,也让他在病友中有了威望 。除了香烟贸易,徐为还承接了康复院上下200多号病人的理发业务 。起初,院长说一个月给徐为30块钱作为理发补贴 。徐为掐指一算,觉得太少,一个月30块,买烟都不够 。他就去和院长谈价钱,说全院200多个头都是我理,少说也要给我一天一包大前门吧 。软磨硬泡下,院长答应每个月给他60块 。给200多个人理发,每个月只收60块,这样的事情若是放到康复院外面,简直不敢想象 。但对于康复院里的徐为而言,这却是来之不易的、通往自由之路的铺路石有了身份,有了人脉,有了特权,有了威望,还有一点小钱的徐为成为了康复院里的病头 。但徐为并不贪恋这康复院铁门内的荣华富贵,他始终记得自己最初的念头,要走到这铁门外,获得真正的自由 。七2005年,徐为正在自己长远规划的上艰难前行 。4月的一天,他和总务站在院子里,看见一辆车停在康复院的铁门外,一个工作人员正把一个年轻姑娘一把从车里拽下来 。有经验的病友都知道,那个被拽下来的姑娘即将加入他们 。徐为第一眼看到那个姑娘时觉得她还像个孩子,就跟总务说:“哎呀,怎么连小孩子都送进来 。”后来别的病友告诉他,这个新同伴只是显得小,其实已经结过婚又离了婚,孩子都16岁啦 。这个新病友就是春春 。她看起来确实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带着一点婴儿肥,有一双笑起来弯弯的眼睛,说起话来温柔腼腆,就像春天树林里毛茸茸的小兔子 。后来,春春成为了徐为的女朋友,二人在康复院里同甘共苦地相伴了十多年 。徐为的说他和春春属于一见钟情 。如果他们相信丘比特的存在,2005年的那个春天,一定有一个瞬间,他的心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两人分开住在不同的病房,只能每天放风的时候在一起玩 。康复院里的小花园、小操场、还有徐为和总务干活的总务室都是他们约会的地方 。徐为干活的时候也会带上春春,两个人配合起来做事麻利,时不时会故作嫌弃地对形单影只的总务说:“你怎么这么磨蹭!”丘比特之箭不仅连起了两个人的心,也让康复院里的医护们乱了一下方寸——公然在精神康复院里谈恋爱,这可是件大事 。医护们团结一心要让这样的事情空前并且绝后 。于是,护士们每次看到徐为和春春坐在一起,就会说:“分开,不能坐在一起!”医生们更凶,每次康复院召集病人们开大会小会,医生也会明里暗里、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地抨击他们的恋情 。即使无法将他们分开,也要补上一嘴:“就你们俩?做梦去吧!”康复院里的医护仿佛变身成为中学里抓早恋的教导主任,而徐为和春春把一切阻拦当作耳旁风,硬生生顶住了一切压力 。春春说:“这一路,是我们闯出来的!”她一向腼腆,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就像一个和教导主任斗智斗勇、最终因爱得胜的高中女生,眼睛里闪着星星 。丘比特之箭在徐为的长远规划上打了一个转向 。但徐为并没有因为爱情就打算放弃逃跑,只是计划有变,他决心要两个人一起出去 。八想要两个人一起逃出去,徐为之前的长远规划就要修改 。首先是要存钱,最主要的是存钱 。在徐为看来,最重要的就是钱,钱,钱 。在之前的规划里,钱还没有那么重要 。如果逃出去,自己一个人到东到西没有牵挂,只要有一点钱不至于饿死就可以 。但有了春春,一切就不一样了 。在新规划里,他们出去肯定不可能很快找到工作,所以要有一笔存款让他们能够租房子,买好一点的衣服……徐为自己不介意风餐露宿,但他一定要让春春干净体面、有个屋檐 。于是徐为想尽一切办法在存钱的路上狂奔 。一边是节流,徐为基本不怎么用钱,连烟都抽得少了 。食堂里卖五块钱一份的水果,别的病友一天吃两三份,徐为就买一份,给春春吃 。一边是开源,徐为的香烟贸易已是康复院里的老字号,每一单赚三块五块,他又利用自己的人脉开拓了餐饮业务——帮病友从康复院外面买生煎点心带进来,每一单赚一块两块 。多年以后,当春春被问到,当时怎么就这么相信徐为,怎么就不担心他卷走他们一起存下的钱自己远走高飞呢?春春只是笑 。老徐每天会和春春报告说我们存下多少钱了,存到多少钱我们就出去 。和徐为不一样,春春家里人会定期过来探访,想要出去不会那么难 。可是她家人当时无法接受她在康复病院里遇到的爱人 。所以,春春还是死心塌地地决定和徐为一起逃跑 。除了钱,徐为的长远规划里还有一件头等大事——自由出入康复院的特权,还得是两个人的 。这样的特权必然能让逃跑大计如虎添翼,但这种特权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徐为苦心经营的模范病人人设再一次起了作用 。有一次,康复院的护士选中了徐为让他陪同病友外出看病 。这,就是特权的开始 。康复院地处偏僻,每次有病友要出去看病的时候,徐为都要走到附近的大马路上去帮护士和病友打车,到了医院以后,挂号一类的事也都由徐为包办 。虽然心中切切渴望的自由就近在咫尺,但徐为还是稳稳地沉住了气,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想要借机逃走的样子 。一次、两次,当徐为每次协助护士陪病友外出看病,办好事又规规矩矩地回来的一年多以后,徐为自己终于有了外出的特权 。跟医生护士打一声招呼,他就可以出去溜达一圈,帮病友买一点生煎点心,只要当天回来就可以了 。他还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康复院附近两家不同的银行,给自己办好两张银行卡,把之前和春春一起攒下的钱存进了不同的银行卡里 。走得最远的一次,他搭上地铁,直奔市中心 。这也是徐为长远规划里的一部分,去市中心的核心任务是购物 。他给自己和春春买了几件比较贵的衣服,又花了300多块钱给春春买了一双好一点的皮鞋 。徐为觉得逃出去以后至少要穿得像个正常人,不能让别人一看就猜到是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 。除了置办正常人的行头,徐为还做了一项重大的投资——买手机 。那时,他们两人靠着这里一块那里两块的攒钱,每个月最多只能攒几百块,花钱的时候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 。但在买手机这件事上,徐为毫不含糊,大手笔斥巨资1980块,买了一个能打电话、能看电视、能上网的智能手机 。康复院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更没有哪个病友有手机 。在这样一个被信息时代遗忘的小世界里,拥有一部智能手机的徐为简直像一个高科技傍身的未来人 。为什么要一下花掉几个月才能攒下的钱去买一部智能手机?这里面有徐为的深谋远虑 。要想顺利出去,他们就需要随时关注新闻,万一新闻里“通缉”他们了,他们就要赶快想对策 。所以,一个能打电话、能看电视、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并不是奢侈品,而是他们的刚需 。在那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事情让徐为非常伤脑筋:“我是有特权的,可以随便进进出出,可是我要怎么带着春春这么一个大活人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一起出去呢?”绞尽脑汁,他们俩想出了一个点子:买早点 。徐为长期在康复院里发展餐饮业务,他出去买个早点顺便帮病友带一点,谁都不会觉得奇怪 。他决定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在买早点的时候带着春春一起出去 。有一天凌晨四点半,徐为和春春走到康复院门口,跟门房的值班阿姨说,他们肚子饿了,要出去买早点 。值班阿姨知道,徐为出去买早点是正常的,可他要带着春春一起去,就不符合规定了 。但那时他俩恋爱已经四年多,是康复院里的模范情侣 。值班阿姨便全当是热恋中的小情侣黏着对方,睁只眼闭只眼地放他们出去了 。致力于长远规划的徐为当然不会在第一次买早点的时候就带着春春有去无回 。他们不仅规规矩矩地回了康复院,还给值班阿姨带了一份早点 。从那以后,他们每天都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一起出去买早点,每次都给值班阿姨带一点,每一次买完都规规矩矩地回来 。就这样,他们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让所有的值班阿姨都习惯了他们凌晨四点半一起出去买早点的行为,并且相信他们只是单纯地出去买早点,一定有去有回 。有了必要的装备和特权,徐为开始担心他和春春的身体 。要有好的体能,这是顺利出逃的本钱 。大约在2010年前后,徐为就在康复院里放出风声说:“哎,我这身体也是越来越差了,是时候要锻炼锻炼了啊 。”放了一阵风后,徐为和春春便开始在康复院里锻炼身体 。他们不敢一下子锻炼起来,怕这变化太大,引起医生和护士的怀疑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每天早晨绕着康复院的小操场跑半个小时 。等医生和护士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他们每天跑步的行为后,他们再循序渐进地增加强度,最厉害的时候每天跑上六七圈 。那时自徐为和春春启动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起已经过去了五个春秋 。他们用五年的时间,基本落实了出逃大计里的每一个环节——攒下了近三万块钱、买了智能手机、有像样的衣服裤子、能在早晨四点半手牵手光明正大地走出康复院 。最重要的是,他们仍然在一起,是彼此最信任的人 。在这五年间,徐为其实有无数的机会独自远走高飞 。他有自由走出康复院的特权,身上有身份证、银行卡、手机、钱 。若是换上一套像正常人的衣服,隐没进康复院外的滚滚人潮里再也不回头,或许也就从此自由了——那是徐为渴求了很久的自由世界 。只是那个自由世界里没有春春,他便一直没有进去 。九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这是徐为和春春准备出逃的日子 。那时候火车实名制刚刚推行,徐为用手机上网查到春节假期结束的第一天,买火车票没有严格的实名制 。他们的目的地是广州,因为那里的冬天暖和,不用花很多钱买厚的衣服裤子 。生活也相对便宜,实在碰到困难找不到住处,还有可能在外面扛一扛,不像寒冷的城市,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出逃前夜,徐为和春春仍然在各自的病房里,脑子里和心里满是兴奋和紧张,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大约凌晨四点,徐为起床,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一样,他们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手牵手走到康复院门口,告诉值班阿姨,他们要去买早点 。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一样,阿姨打开了康复院的铁门 。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不一样的是,他们心里知道,这将是一次有去无回的“买早点” 。剧照 | 《飞越疯人院》一出康复院的大门,他们便立刻到附近的大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银行的ATM机 。徐为从两张银行卡里共取了一万八千块,加上他们手里原有现金,总共有差不多三万块 。他一早就想好,出逃的时候不能用银行卡,要用现金,这样才不容易被人找到 。取完钱,他们又拦了一辆出租车,冲向上海南站 。到达南站的售票处,他们买到了早晨9点10分发车前往广州的火车票 。一切都如徐为计划的那样,一气呵成、畅通无阻 。终于,徐为和春春一起逃出了康复院,真真切切地站在距康复院十几公里的上海南站里,手里攥着南下广州的车票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此刻已经完成了99%,就等时候到了,火车进站 。一旦踏上那辆火车,从此都是自由 。早春凌晨的上海南站还是漆黑一片,大部分店都没有开 。徐为和春春觉得又冷又饿,就在车站小卖部里买了两碗泡面,果腹、取暖 。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和凌晨出逃的一路颠簸,之前的兴奋和紧张在此刻都化作疲乏困倦朝他们涌来 。他们坐在南站候车厅的座椅上,渐渐打起了瞌睡 。徐为在心里知道这是不对的 。他想:“我们不应该坐在固定的地方啊,我们应该换位置,应该不断地绕着南站兜兜逛逛,只有这样,我们才不容易被人发现,才安全 。”可是他实在太困了,一点都挪不动了 。好像又有人在他脑子里打出一行字幕:“不能坐在这里了,有人在找我们 。”可是他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和春春就这样在上海南站候车室的椅子上睡着了 。他们被人推醒的时候大约是早晨七点 。睁开眼,站在面前的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人——康复院的医生 。医生边上还有一个护士,两个人,也没有说话,就站在他们两个人面前 。这些年的一切都戛然而止,没有人能明白徐为和春春在那一刻所体会到的绝望 。徐为对春春说:“安静一点,跟他们走 。他们只要指着我们大喊一声精神病,我们硬逃也不可能逃掉 。”十徐为和春春被医生抓回康复院 。他们一个被关在康复院的第一间,24小时候不关灯,另一个被关在康复院的最后一间,24小时不开灯 。徐为被关在不关灯的那间,晚上也明晃晃的,根本睡不好觉 。没有其它事情可做,他就在房间里跑步,跑房间的对角线 。康复院里医护们勒令徐为和春春分手,否则就一直关禁闭 。他们俩被分开紧闭,没办法互相通气,但都态度坚决:“我们绝对不分手 。”医护拗不过他们,关了一个星期后,就把他们放出来了 。靠自己逃不出去,徐为便开始联系媒体 。他给各个大小媒体打了一轮电话,只要是能查到号码的,他都打了一遍 。有一些根本不理他,有一些告诉他会找采访人员跟进,但之后就没有采访人员再来联系他 。他又去找残联,希望残联能够帮助他出院 。但是残联的负责人对他说:“你是精神病人,你要叫你的监护人和我谈 。”徐为听了觉得荒谬,就是监护人把他送进来的,怎么会愿意接他走?早在很多年前徐为就符合康复院的出院标准了 。但是,康复院的惯例是“谁送来谁接走”——谁把人送进这康复院,谁就是康复院认定的监护人,即便一个人符合康复院的出院标准,只要监护人不肯接走,康复院就不会放人 。
以上关于本文的内容,仅作参考!温馨提示:如遇健康、疾病相关的问题,请您及时就医或请专业人士给予相关指导!
「四川龙网」www.sichuanlong.com小编还为您精选了以下内容,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恋爱中的精神控制有多可怕 如何摆脱感情中的精神控制
- 什么是精神出轨呢 精神出轨可以原谅吗
- 忘不掉前任算精神出轨吗 对前任念念不忘算精神出轨吗
- 电击治疗精神病有效果吗
- 精神分裂症的后遗症有哪些啊?
- 精神分裂症中医能治痊愈吗?
- 恋爱中女生精神出轨的表现 如何分辨女友是不是精神出轨
- 什么程度算精神出轨 如何忘记出轨的事情
- 得了轻微精神分裂症好治吗?
-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主要表现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