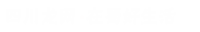“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 。兵戈沸处同国忧 。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 。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 。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 。”这首散曲是宗璞先生自述生平的游戏之作,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却是她创作的艰辛与执著 。
宗璞在嘉定看病时,听她慢慢地向医生叙述自己的病情,真的觉得这句“从来病骨难承受”并非虚言 。因为从小体弱多病,宗璞做过各种各样的手术,因而得了个外号:挨千刀的 。《东藏记》的写作开始不久,她的视网膜脱落,经过手术幸未失明,但是左眼仅有0.3的视力,右眼几乎看不见东西,说是“准盲人”实在不为过 。近年来,相依为命的老伴去世,宗璞的头晕顽疾更加重了,劳累过度时会天旋地转,加上左手时常麻木痉挛,她已经无法长时间阅读和用笔写作 。
虽然身体的顽疾带来的是许多的不适和不便,但并没有阻止宗璞对写作的热爱 。她戏称自己是“三余作家”,因为多年来她的写作只能在业余、事余和病余进行 。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她的作品几乎篇篇是同疾病斗争所得 。不能执笔写就口述,由助手记完一段再念给她听,一节完成再打印出来给宗璞看,当然,字号也必须放大到一号 。难以想象宗璞先生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一点一滴地完成了线索纷繁、人物众多的《东藏记》 。她说自己“像一只蚂蚁,很小的蚂蚁,认真努力地在搬沙,衔一粒,再衔一粒,终于堆起一座小沙丘” 。
如此重病缠身,何以还要对写作不离不弃?宗璞先生也承认:“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 。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 。”但是,她说:“读小说是件乐事,写小说可是件苦事 。不过苦乐也难截然分开 。没有人写,读什么呢?下辈子选择职业,我还是要干这一行 。”
宗璞先生从父亲身上承继的不仅仅是日后文学创作的积淀,更是一种坚韧执著的写作精神 。冯友兰先生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80多岁,年老多病,起先还能自己写,以后就只能口述,在助手的帮助下用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 。薪尽火传,这脉脉文心在曾经长期侍奉左右的宗璞的精神中一脉相承 。在母亲、父亲、丈夫,这些生命中最亲的人一一西去时,宗璞依旧继续着自己的写作和生活 。她选择了父亲的书房做书房 。当年冯友兰失去目力听力后,就是坐在这个房间里慢慢地写着的 。而如今,宗璞也在这间书房里,长年抱病写写停停,迎接着生命长河中的一波又一波 。她说:“我坐在父亲的书房里,看着窗外高高的树,在这里,准盲人冯友兰曾坐了三十三年;无论是否会成为盲人,我也会这样坐下去 。”
宗璞先生说,写《野葫芦引》是来自于一种留住一段不被歪曲的历史记忆的使命感 。年少时随父兄辈南迁,这段铭心刻骨的亲身体验成为了她创作《野葫芦引》的丰富素材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她就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来刻画出西南联大师生们身受亡国之痛、流离之苦,却依然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己任的精神品格,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动笔,不过小说的人物已在她心里经过了千锤百炼 。经过15年的心血浇灌,两个“野葫芦”——《南渡记》与《东藏记》终于“长熟”了 。
那天,她带着这两个耗尽心血“培育”的“葫芦”来到复旦大学,听沪上一些作家、评论家的点评 。整整三个小时,病人宗璞带着助听器,如石佛般静坐,倾听各位的高论 。
宗璞认为:“历史是个‘哑巴’,靠别人来说话 。人本来就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写的历史 。我写的这些东西是有‘史’的性质,但里面还是有很多错综复杂的我不知道的东西,那就真是‘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了 。还是把人生看作一个‘野葫芦’好,太清楚是不行,也做不到 。”“我还不能说这是个野葫芦,只能说是一个引子,引你去看人生的世态 。”一句话道出了书名的来由,其实,小说最初名为《双城鸿雪记》 。
以上关于本文的内容,仅作参考!温馨提示:如遇健康、疾病相关的问题,请您及时就医或请专业人士给予相关指导!
「四川龙网」www.sichuanlong.com小编还为您精选了以下内容,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百思买的游戏笔记本电脑交易带回超便宜的RTX3060MSIGF65
- 惘然无措、惶惑不安的意思? 惘然无措的意思
- 跑步机锻炼时的误区
- 6种最常见的增肌健身计划
- 搬家当天买什么鲜花好财运亨通的花篮
- 现代搬家最简单的风俗 讨个吉祥如意的好兆头
- 让你惊叹的“网络健身”
- 搬家要带的6样东西 带火柴有什么寓意
- 哑铃锻炼你全身的肌肉
- 哑铃健身的3大误区